《梁漱溟问答录》一书1988年首次问世,一时成为畅销书,颇为抢手,印数不少,似有些洛阳纸贵的味道。之所以如此,一方面是有需求,一方面是此书部分内容有可贵的史料性质(即笔者所说的“独家旧闻”)。2004年此书增订再版,内容又有增加。由于先父梁漱溟为此书中“主人公”,而笔者作为“主人公”的亲属
从“第一印象”说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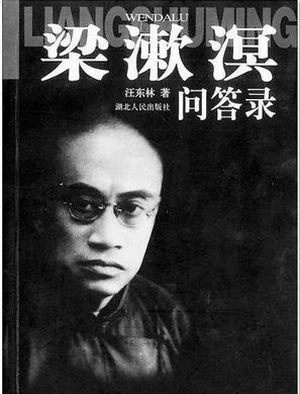 笔者初读此书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:看来这是一本以梁漱溟为传主的“口述自传”。请看,全书自开篇至结尾,一“问”一“答”,随着一个个“提问”,一个个“作答”,梁漱溟就这样地亲自“口述”了个人的家世与生平。那么将其视为一本梁漱溟的“口述自传”,谁说不宜?可是随着阅读次数增多,与细节了解的深入,遂察觉此书与“口述自传”这一印象有诸多矛盾,于是产生了一种疑惑,疑惑自己可能犯了一种“顾名思义”的错误,即将“问答录”误为“访谈录”了。
笔者初读此书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:看来这是一本以梁漱溟为传主的“口述自传”。请看,全书自开篇至结尾,一“问”一“答”,随着一个个“提问”,一个个“作答”,梁漱溟就这样地亲自“口述”了个人的家世与生平。那么将其视为一本梁漱溟的“口述自传”,谁说不宜?可是随着阅读次数增多,与细节了解的深入,遂察觉此书与“口述自传”这一印象有诸多矛盾,于是产生了一种疑惑,疑惑自己可能犯了一种“顾名思义”的错误,即将“问答录”误为“访谈录”了。
“问答录”与“访谈录”,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是如此难以区分,其相似可说真能“以假乱真”。笔者一度将二者混淆不分,与此有关。而实质上二者是根本不同。“问答录”是一种文字作品。它以作者摘取素材,用问答体的形式编写而成;其中的“问”为作者的“设问”,其中的“答”是依据素材编写而成,并非二人的真实一问一答的记录。“访谈录”是一种口述作品,它是以真实的采访所得为材料;其中的“问”为访问者的“提问”,其中的“答”是被访者的口述真实记录。由此可见,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;其相似只是形似而已。显而易见,《梁漱溟问答录》并非是一部口述作品,而是一部文字作品。它仅在文字形式上与“访谈录”相似而已。既然它的产生来自作者的编写,是作者撰写的一部传记作品而并非传主的本人口述作品,这又怎能称之为“口述自传”呢。
可见自己的“第一印象”是不对的。可是误以为此书为梁漱溟本人口述的真实记录,是他自己的著作,与笔者犯有同样的错误的似大有人在。2003年中国数字图书馆送来“授权作品列表”一份,将《梁漱溟问答录》作为梁漱溟本人的著作,列入其中,即是一例。
从本书作者自述其写作经过中,也透露了此书并非是一本“访谈录”;只是未从正面着重加以说明。在此书1988年版的《后记》中,作者说他是在两位中年作家的“鼓励”和“支持下”,“采用问答录形式”来写此书的。此书出版十年之后(1998年),又见作者所写的《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》(《中央盟讯》,1998年,12期),其中写到他原来计划写一本梁漱溟的“十五万字传记”,且已写出“前三章”,约“三万字”,才改变了主意,“将原稿作废”。放弃“第三人称”写法,“改为第一人称的‘问答录形式’”,用“一个个作者问,梁作答的形式,反映梁先生一生每个阶段的重要思想、言论和行动。”读了这些之后,笔者更加醒悟不应将“问答录”误当作“访谈录”了。可惜作者这些自白的话,刊于民盟内部刊物,读者多无缘见到。
错误“印象”的再纠正
“第一印象”初步纠正之后,笔者又将书中的“答”话内容,所取素材的出处一一加以查对,于是更清楚地认识到将此书当作是“访谈录”,完全是一种误认。
依笔者所见,此书采用素材之出处有四:
一是梁漱溟本人所写的自述性文字。如“谈”家世,“谈”求学经历等,摘自《我的自学小史》。如“谈”蔡元培先生,素材取自《纪念蔡元培先生》一文。“谈”访问延安,素材取自《我努力的是什么》。“谈”会见泰戈尔,其内容取自《道德为人生艺术》等等。
二是全国政协会议、学习会上梁漱溟的发言或谈话记录。如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的表态、发言等,均以当年的会议记录为根据。笔者称之为可贵的“独家旧闻”的那部分内容,其素材即取于此。
三是存档的资料。如“补遗六”一文,即以1958年梁漱溟《政协整风小组会向党交心的发言》(打印件)为素材。
四是作者对梁漱溟采访所得。这是对上述三类素材的一种拾遗补缺工作,是真正的口述实录内容。如此书中谈八国联军入京后的见闻,即属此种采访所得。
由以上所述可见,此书大部分内容的素材取自已出版的梁漱溟的著述,小部分取自会议记录等,而真正的采访实录,估计不超过十分之一二。因此,作者不将此书称为“访谈录”,而名之为“问答录”,是“名实相符”的。
虚构导致失真
以问答体写作,少不了要对素材作一番文字加工。原来的书面语言,就须使之口语化。还有较为难办的是将全部内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表达。显然,此种形式是虚构性的。作者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,大体上是成功的,但也有欠妥之处。例如:
“……十多名政协委员……居然一条意见也提不出来,是不是有失自己的身份,想到此,便顾虑顿消,举手要求发言……”(指1970年讨论“宪法草案”时发言)
讨论“宪法草案”,为什么梁漱溟要发言?那是因为早在上中学时,他即热心国家的政治改造,注意学习与宪政有关的国会制度、责任内阁等知识,尤醉心于英国式宪政。英国为宪政政治的始祖,其宪法始于限制王权,即不允许任何个人权力凌驾于与宪法之上。这是有关宪法的基本常识。“宪草”将个人名字,如将林彪等写入其中,显然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精神。他自己对此知之十分清楚,当然“不容自昧”,只能直言,如此而已。这与怕有失政协委员“身份”有何关系?又如:
“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,在当时却有震惊四座的劲头……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,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,不知说什么才好。”(所说“意见”,指讨论1970年“宪法草案”时所说的不赞成将个人名字写入其中,及不应缺少设国家主席一条。)
类似的“话”在此书的旧版中更多。如“我的最后答复,震惊了各组同人”(指“批林批孔”中,以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作答。)又如“我这篇发言,当时使人很震动。”(此发言指毛主席搞的是人治,这种搞法已走到了尽头,今后将步入法治才是。)这种“话”,依笔者所见,是有虚有实。“实”是指到会者反应强烈,是实情。“虚”是指此话出于梁漱溟之口,是虚构。以虚构形式“强迫”梁漱溟说出他本人不会说的东西。事实上,他如实说出自己的所见时,早将个人得失毁誉置之度外,又何曾在意与会者什么“震惊”不“震惊”?
然而还有因虚构而导致的另一种失真,更令人难以理解。这就是此书作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,甚至所感,全部“勉强”梁漱溟为之“代言”,而作者本人却坚持身居幕后。此类情况不少。现仅举一例:
“这一闹腾,我也深感失言……我甚至想到进监狱……。”“不料几天后……会上宣布……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……可以不必纠缠。于是我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。那么这‘上级’又是谁呢?……我同样不敢深问……军代表没有这种胆量……。那军代表之上又是谁呢?自然是周总理办公室……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对的。”
以上种种,对梁漱溟来说真是不知从何而来。难道他确因对“宪法草案”提意见感到“失言”而后悔过?事后确曾为个人安危而担忧?是否曾猜测过上级将伸出援手?……这可以用以下的话来回答:
“年来胸怀只有尽我责任一念,相信一切皆在天命中。假如有什么祸福、荣辱、得失到来,完全接受,不疑讶,不骇异,不怨不尤。我态度坚定,兄不难看出。”(《梁漱溟致王星贤》1974年6月3日)
将此信内容与上面那些作者所编写的话相对照,我不得不承认对先父梁漱溟而言,那些话从形式到内容,均属虚构。这种双重的虚构必然导致严重失真。
可能是作者感到如上这样的虚构欠妥,在此书新版中已将这些内容改用第三人称表述。写入“补遗七”之中。
“失真”存在的缘由
对于这类“失真”,察觉不难,而纠正却又非易事了。首先,由于此书作者有其两难之处:一方面,第一人称写法必须坚持,不能放弃,而另一方面又有自认为重要的素材,不忍割舍。而在《问答录》问世之前,作者所写的有关梁漱溟的文字(如《梁漱溟先生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》,1986年),由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写法并用,不拘泥于第一人称,即不存在这类“失真”。这就从正反两面说明了此类“失真”得以存在的一个缘由。
“失真”得以存在的另一个缘由,显然是由于审改环节的疏失,而此事先父似难辞其责;至少有一部分责任。此书作者写得很清楚:“每一章都经梁漱溟先生亲自过目审改。”(见此书新版《后记》)作者又曾写道:“1985年初,我已完成《梁漱溟问答录》一书初稿15万字。我一章一章地请梁漱溟老人亲自审定。”(见《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》1998年)如此看来,送审当在1984?1985年间。全书十一章,其中十章送来当在此时(唯第七章不在其内)。此时笔者尚在工作岗位上,又住于郊外的北大宿舍,先父当年是怎样“过目”,又是如何“审改”,笔者均不及见,故不能置一词。可以一说的是,当时先父已届垂暮之年(92岁),头脑尚清楚(临终时犹如此),每日必翻阅书报,却无奈精力不济,精神集中难持久,伏案工作早已停止。对文字的推敲修改,先父一向极为认真仔细,总是字斟句酌,但此时对这十章的审改似难以再如此讲求。设若不然,那为何一些明显差错竟未发现。
此书第七章《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》(内容为1953年之事前后经过),据说因事关“敏感”,写定最迟,送来也最晚(1987年初)。恰好笔者于是年退休,得常去先父处,并有时留住,因此有机会参与此章的审改事。审改的进行由笔者先作初步涂改,然后逐段与先父商讨改定;如此分三次完成。据笔者日记,改毕之日为1987年3月13日。不过,待此书问世,将书中第七章与笔者保存的有涂改之原件(复印件)相对勘,修改意见被采纳者是有限的。
书中“失真”存在的缘由,就笔者所知,仅限于如上所述。
严重失实引发“空穴来风”
因记述严重失实,而审改又失察之一事,有必要一说。
此书旧版第九章最末的“问”与“答”中,以梁漱溟的“语气”,不点名地批评了“北大某教授”,引起冯友兰先生家属的强烈不满,很快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文章,以委婉的语气,指出先父有“记忆果然移形若此”的错误。不满是理所当然。因为所记冯梁二位这次“会见”的前前后后,失实严重。失实之处主要有三:
首先,“会见”时间完全搞错了。“会见”明明白白是在1985年12月24日,却写成了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(即1973年~1974年),前后相差竟达十年以上。
其次,“会见”的由来写错了。是1985年尾,冯先生邀请先父出席其九十寿宴,为先父所拒绝引起的,而书中所写,是由于先父“写信批评”冯先生,并要冯先生“答复我何以这么作”所致。对于冯先生于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之所为,先父无法理解,确实极不以为然,但他从未在任何场合发言,批评过冯先生。学习会上“学习”冯先生的批孔文章时,对这是否是冯先生的真心话,仅流露过怀疑之意,并在日记上写下“可叹!”两字而已。如有严厉的表示,也仅限于因友人询问而在信函中,写上一两句。背后议论他人短长,说三道四,先父一向无此“习惯”;虽与家人之间,亦不例外。事实是自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开始,直至“最后一次会见”,前后有约十年间(1974年~1985年),二人无任何往来,以书信或当面口头批评冯先生之事又何由发生?可见二人“最后一次会见”说是因“写信批评”所引发,只能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事了。
再其次,“会见”经过写得明显失实。冯先生父女二人“乘北大汽车处的车”,前往木樨地22楼先父住处,却写为“悄悄的”去会见。至于意见的交换,实际早已见之于临“会见”之前三两次往来的书信中,而且,“会见”前数日冯先生寄赠的《三松堂自序》一书,先父已过目,其中冯先生自我剖析应“修辞立其诚”的话,自然也已了然。相见时,冯先生表示“批孔”中之事,书中已说清,看了自可明白。对此,先父只是静听,未做任何表示。此后,二人遂转入其它话题,未再涉及“批孔”一事。倒是宗璞女士十分认真,就冯先生于“批孔”中之所为及有关情况,作了若干说明与解释,谈话颇多。而书中所写“叙述他的理由,包括他的苦衷”等,均未曾见于“会见”中。
因记述严重失实,由此竟引发了类似于“空穴来风”效应。于是冯梁二人的“最后一次会见”,一时成为人们议论不少的话题,竟先后有多篇文字发表于报刊;文中或由于虚实难辨,而表示“迷惑”、“费解”之意,或因以虚为实,而流露“惋惜”、“遗憾”之情。这自然都是失实引起的。
笔者有感于已造成失实,无论是因未审而未改,或审而未改,审改者总应负一定责任,特写出《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》(《博览群书》2002年9月),将二人交往经过,自1917年初次相识说到“最后一次会见”,以正面纪实,澄清记述失实,其主要用心在使人们明了事实真相,不再为此枉费笔墨,或浪费感情。
如今此书作者写有《冯友兰与梁漱溟》一文,以“补遗”形式增补于此书新版,也是一种更正的表示吧。同时此书旧版第九章最后以先父语气写成的那段“答”话,作者也依照事实作了不少修改,只是令人不无遗憾的依旧保留了,以先父的语气说的一句话“冯先生如今回头来看看,应该说可以做出一个他自己满意,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。”这话在二人“最后一次会见”前是不会说的(他只是说过“可叹!”);而在“会见”后又何须再说什么。
“独家旧闻”与“有心之人”
如本文标题所示,《梁漱溟问答录》是一本瑕瑜互见的著作。这是笔者的浅见。以上笔者着重陈述了书中存在的诸多瑕疵,及其产生的原由,但终归是瑕不掩瑜。所说之“瑜”,即笔者称之为“独家旧闻”的那些内容。这是此书最可贵的部分。
听说过有“独家新闻”;“独家旧闻”则是笔者的杜撰。“独家新闻”出自捷足先登的记者,其本领在“抢先”,“独家旧闻”则出自别具慧眼的“有心之人”,其所长在“抢救”。“抢救”这些“旧闻”的“有心之人”即本书的作者汪东林先生。
如作者所自白:他自1963年至1983年间,除“文革”中政协被“封门”的四年外,“梁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,到全国政协参加会议和一些活动,尤其是参加作为政协重点工作的学习改造,每周有两三次,我正好是他所在小组秘书。”“他在这20年间政协大小会议上的言论,大部分都由我直接参与记录、整理、写简报。”而这些记录等均在作者所“保存至今的近百本会议记录本”中。(以上均引自《20年难忘写梁漱溟》)
正是作者以其所拥有的这些第一手资料,以及当年其现场见闻为素材,在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,陆续披露了许多“独家旧闻”,如《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》(《团结报》1986年)、《梁漱溟与毛泽东》(《文汇月刊》1988年1月)等。随后又于1988年4月出版了《梁漱溟问答录》,对这些“独家旧闻”作了集中披露。由于当年这类“旧闻”不得外传,均属政协“内部消息”,如今一旦披露,即具有闻所未闻的轰动效果,引起人们极大兴趣。
至今,已问世的有关先父梁漱溟的传记作品约有十种以上,其中以《梁漱溟问答录》为最早,其余的均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陆续出版,而这些后续的传记著作,为描述传主解放后,特别是“文革”时期的言行与处境,均莫不引用《梁漱溟问答录》中所披露的那些“旧闻”中的某些内容。之所以如此,正表明了这些资料是为其“独家”所拥有之故。
说“独家”拥有,还有一层意思。关于这些“旧闻”就是先父本人亦极少有文字留存下来。在他的日记里虽有只字片言,亦难知其详。例如“考虑宪法意见写出两条”(1970年7月26日)“到政协讨论宪法,对第三章只提一条意见。”(1970年7月29日)如此记载,又怎能寻得提了什么意见。虽笔者作为亲人家属,亦难说清楚,因为先父从政协参加会议归来后,从不以会内见闻或个人发言为谈资,与家人闲谈。所以关于先父梁漱溟对1970年“宪草”曾提出过无人敢提的那两条意见,家人了解其内容,也同样是在读到作者所披露的“旧闻”之后了。“旧闻”其他内容,其作用对笔者来说也多与此类似。
先父曾说,他是一个有思想,且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。他又曾说过:“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,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整个的,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”可不幸的是他最后的三十多年,却生活在一个思想受禁锢的环境里。而“文革”十年,黑白混淆,是非颠倒,更是令他陷入困厄之中。而他又坚持“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,以自觉自愿行之。”那么,他将心怀何种理念直面思想禁锢?他将秉持什么态度去面对无理责难与围攻?他的回答是:“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,无所畏惧,一切听其自然发展。”(《致香港友人周植曾》1975年3月28日)这需要具体生动的事实来为之作说明。而能提供这种具体生动事实的,正是那些“独家旧闻”。由此又可见出这些“旧闻”之可贵了。在此可补充一句话:这些“旧闻”不仅对了解与研究先父梁漱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实,而且对了解与研究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,也未尝没有重要意义。
“你的书(指《梁漱溟问答录》――笔者)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,有意义啊。你是个有心之人,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,值得我学习。”(见此书“补遗九”)这是赵朴初老先生的话。赵老这话不是随便说的,是很有分量的。
赵老与此书的作者相识,更与先父梁漱溟有“同窗”之谊。他们二人一个时期曾同在一个学习小组,一同参加运动,有关先父当年在政协活动中的言行,赵老自然是知情人,即对“旧闻”中所记录的那些内容有亲历直接的了解,故深知其可贵。赵老的话正是由于有如此深刻了解,才这样说的。因此,笔者愿借赵老这句话作为对此书评说的结束语。
(《梁漱溟问答录》,汪东林著,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,25.00元)
